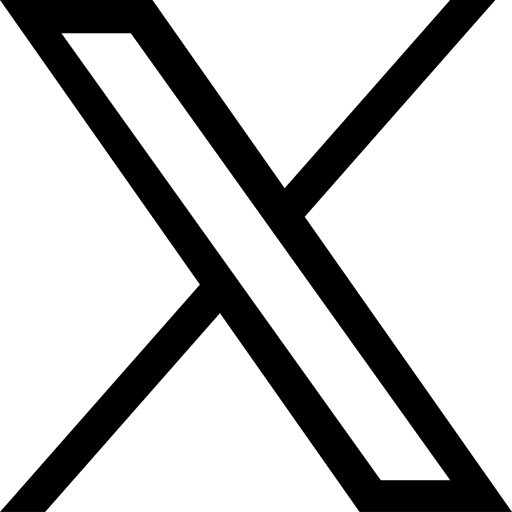2011-07-21
哭我城牆
這是一篇以前寫下來的文章,於以色列一遊之後,以色列的耶路撒冷,特拉維夫,死海古卷等引來不少的反思,我很喜歡這篇文章,再次與你們分享。
昨日已逝,明天未來,現在就是我們最好的禮物。
以往的香港,只向著未來,舊建築相繼的被拆去或更新。
現在我們開始留意保留建築古迹。
中環天星碼頭被拆後,城中「集體記憶」突然成為熱話。
難道保留舊建築只是為了虛無的「集體記憶」?
既然過去的已逝,人又為甚麼要執著過去?
世人若只留戀當年,社會又怎會進步?
只是以「集體記憶」為保留舊建築的依據,可能帶來一股「保守」的態度,反使「保留舊建築」的真正意義出現偏差。
「集體記憶」,實在不關乎過去,而是人們現在此刻的價值取向。
建築是可見的硬件,它是人文精神、價值、觀念的盛器。有形的建築,亦是人和社會的足迹。藉着對它的追尋,我們就像進入時光隧道,明白過去的人的生活處境和價值取向。建築反映了人的文化、經濟、政治、社會價值等,本身便是活生生的博物館。
21世紀,世界已進入了極速的消耗期。人類若失去追求「可延續」的目標和為下一代的世界付出的責任感,世界的延續便沒有希望。
城市的公共建築和城市公共空間既然是城市的重要表徵,保留和拆卸有歷史價值的建築或空間,實在有重大的象徵意義。
耶路撒冷的哭牆


以色列耶路撒冷著名的地方不少,位於城中心的「哭牆」最為舉世知名。為甚麼叫「哭牆」?為甚麼此牆是這樣的悲痛?


「哭牆」是猶太人被拆去的聖殿唯一留下的一片牆。聖殿已毀,原地上卻蓋上了伊斯蘭教的清真寺(Mosque)。這個拆去和再建的行為,帶着兩教不能共存、你死我活的意念,反映人與人、宗教與宗教、國與國之間,幾千年來解不開的結和沒完沒了的報復。
07 年 3 月 19 日,在哭牆下仍然看見在牆下哭泣的人。



中環天星的「哭牆」
06 年12 月16 日凌晨,我不想只在電視上遙看天星碼頭發生的事情,於是跑到現場,看見成群年輕人與警方對峙。青年人拿著當天環保署的批文,批文允許承建商即日可進行24小時不停的清拆。這些青年人無路可訴,哭著問政府以甚麼理由批准24小時緊急清拆?照常理,這些緊急清拆都基於公眾安全和利益!
他們知道後更無助。為了公眾安全要全速拆去天星,為的是建一條由人畫出來的路和地底下看不見的渠?他們的悲痛只能發洩在圍著地盤的鐵板圍牆。
孩子們向著牆,無聲地只用手搥著鐵牆,靜默的海港只聽見這些連綿的回響。深夜裏,雨仍然微微地下著,沒有間斷,像為此時哭泣。
為甚麼發出這悲鳴的是一群沒有多少「集體回憶」的年輕人,而不是真的和天星有感情的中產或老人家?因為這不只是「集體回憶」的訴求,而是拆去的是公眾空間,騰出來的卻是可牟利的土地。
地產主導已大大傷害眾人的利益。看看哭牆,千年的怨氣仍在,耶路撒冷仍四分五裂。
天星的「哭牆」仍是無形的存在。
香港的包浩斯建築
中環天星碼頭建於1958年,而位於灣仔的灣仔街市則建於1937年。灣仔街市與中環街市一樣,是香港僅存的「包浩斯」建築。
「包浩斯」(Bauhaus),是源於 20 年代德國的一個影響世界的意念。
包浩斯學院於1919年創立於德國威瑪(Weimar),後再移師至德騷(Dessau)。包浩斯的創見在它把各藝術領域都包括於「設計」此概念之內,而設計的概念有表達當時時代的職責。
建築師Walter Goupius帶動了包浩斯建築,一個表達新時代、新社會主義的建築形式。包浩斯學院在1933年被德國納粹黨封殺後,不少包浩斯建築師轉移到美國發展,後來更成為影響全世界的國際主義(International Style)建築。
特拉維夫的「白色之城」

以色列特拉維夫初建於1909年。在1921年,因為在 Jaffa 舊城內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和,猶太人於城旁另建新城,名為特拉維夫(Tel Aviv),意思是春天的山。特拉維夫的城市藍圖,由當時國際著名的城市設計師 Patrick Geddes 設計。
今天特拉維夫已是以色列第二大城市,城內有大約1,500 座包浩斯建築。2003年,這包浩斯建築群被命名為「白色之城」,更被 UNESCO 認定為世界歷史文物(World Heritage Site)。
特拉維夫建城的時候正是包浩斯的高峰年代,不少建築師都是由歐洲各地回流,深受包浩斯的影響,不少更是直接在包浩斯學院學習的建築師。當年的特拉維夫需要迅速的建立,包浩斯建築的混凝土和簡約設計帶來了經濟和速度上的方便。理念上包浩斯建築是新社會主義的服務者,用作建設特拉維夫大量的工人住宿,是最適 合的選擇。
現今的特拉維夫亦處於改變的途中,保留這些包浩斯建築或重新發展是他們重要的取捨。
直至今天,特拉維夫仍以他們的「白色之城」為傲,他們盡力保留這建築群,並賦予建築物新的用途。
「古為今用」的建築物
於 Dizengof 廣場旁的「戲院酒店」(Cinema Hotel),便是古為今用的一個例子。原本的戲院現改為酒店。保留外貌之餘,原來的電影器材亦成為酒店內的特色,成為城中有吸引力的「精品」酒店。
舊建築作新用途,既不會產生大量建築廢料,又帶來經濟效益。「集體回憶」不是故步自封,而是「古為今用」。過去的事迹成為今天的借鏡,令城市的發展更有深度。
幾千年耶路撒冷的哭牆仍在,人的悲痛沒斷。天星不要重蹈覆轍,讓這怨氣繼續。特拉維夫「白色之城」保留了1,500 座包浩斯建築,而香港只剩下灣仔和中環街市。當它們被拆後,包浩斯建築在香港的足迹亦宣告完全消失。
此刻,我們會為下一代作出甚麼抉擇?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etnet榮獲HKEX Awards 2023 「最佳表現證券數據供應商」大獎► 了解詳情